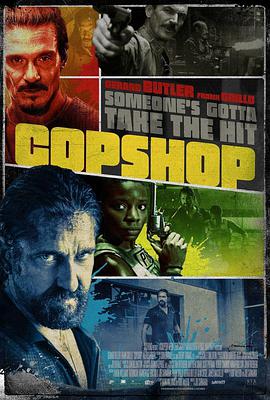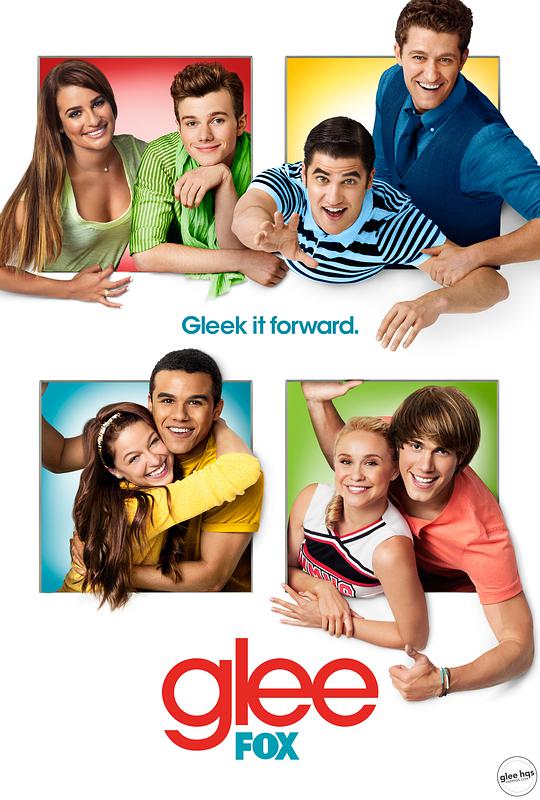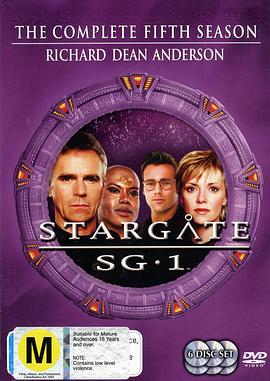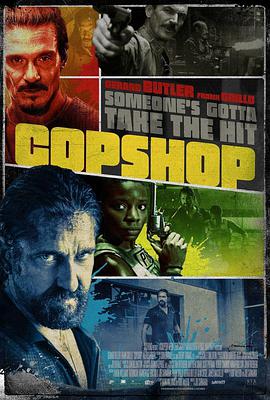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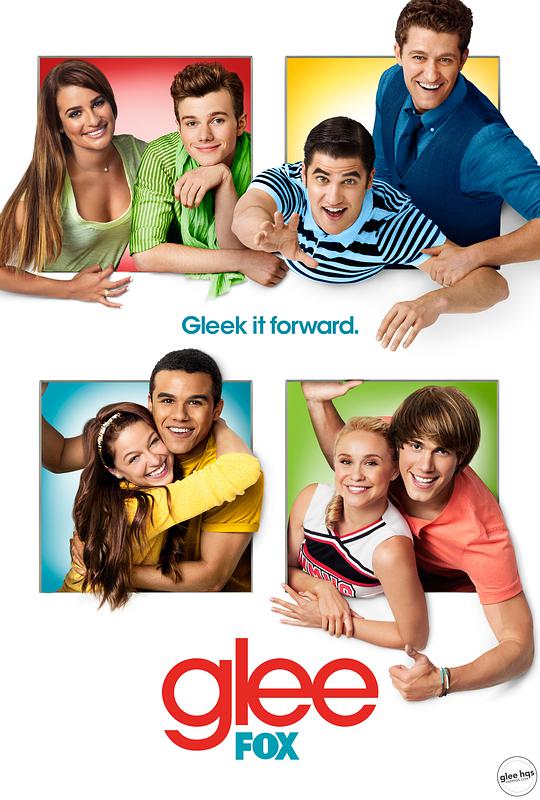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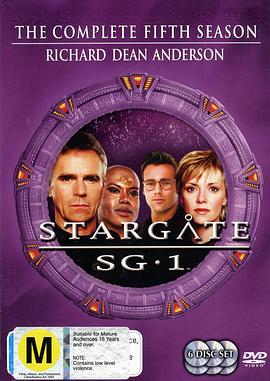








我茫然地向着窗外,望着这无边的、沉默的、纷纷扬扬的白色。天色是沉沉的铅灰,仿佛一块巨大的、未经打磨的砚台,倒扣在人世间。雪,便从那不可知的深处,静静地,悄悄地,来了。它们不像雨,有那淅淅沥沥的、或急或缓的宣言;它们只是飘着,舞着,仿佛是时间本身抖落的、无数细小的、白色的尘埃。伸出手去,想接住一片,看个究竟,它却只在指尖微微一凉,便化作了极细微的一点湿痕,连形状也未曾让你看清,就匆匆地不见了。你凝视着那一点水渍,心里便空落落的,想:这便是它来过的踪迹么?这踪迹,又能存留几时呢?
今日的雪,与昔日的雪,有什么分别呢?它们一样的白,一样的轻,一样的从不可捉摸的九霄,奔赴不可挽留的大地。然而我总觉得,今日的雪,似乎少了些清冷。我说的这“清冷”,并非单是肌肤所感的寒冽,更是心头所触的那一种孤迥与决绝。从前的雪,像是天地间一场盛大的、静默的仪式,带着洪荒以降的寒意,能将整个沸腾的人世,暂时地封存起来,让你听得见自己心跳的声音,听得见宇宙呼吸的节奏。谢安石问子侄:“白雪纷纷何所似?”谢朗说:“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”终究是笨拙了,落了形迹。道韫女子说得好:“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这才有了那份轻盈的、无目的的风致,可这风致里,总还萦绕着旧时王谢堂前,那一缕若有若无的、高华的清冷。那清冷,是竹林七贤酒后的扪虱清谈,是陶渊明东篱下偶然抬眼时,南山之巅那亘古不化的、一点孤高的白。如今的雪,落在这满街的车马喧嚣里,落在五光十色的霓虹之上,仿佛一个走错了年代的、羞涩的客人,那点天生的寒气,还未及铺陈开,便被鼎沸的人声与热浪,融解得气息奄奄了。于是,它似乎只剩下漫无目的的“下”着,温暾暾的,一片一片,填塞着楼宇的缝隙,遮盖着尘土的容貌,却再难冰凉一颗颗在暖气房里浸得慵懒的心了。
然而,雪终究是雪。你若肯静下心来,将耳朵从这室内的嘈杂里抽离,将目光投向更渺远、更空阔的地方,你或许仍能听见,那穿越了浩浩时空的、雪的静默的回响。这静默,是有声音的,且是天地间至大至深的声响。我想起古人说的“雪落黄河静无声”。这是何等苍茫而又慈悲的境界!莽莽黄河,那是我们民族血脉里最雄浑、最暴躁、最不肯安宁的一段乐章。它挟着黄土,吼着秦腔,日夜奔流,是力,是怒,是挣扎,是生命原始的张狂。可当大雪降下,那仿佛能吞噬一切的、绵密的、温柔的白色,竟能将它抚慰得如此沉静。这不是征服,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包容与化解。滔滔的浊浪,在雪花的轻吻下,收敛了咆哮,放缓了奔突,渐渐地,与两岸的寂静融为一体。那“静无声”,不是死寂,是动极之后的静,是纷繁之后的纯一,是天地间一场无言的对话与和解。这雪,便不止是水汽的凝结,倒像是时间沉淀出的、最精纯的“静”的本身,飘洒下来,为这永动的、焦灼的河流,披上一件安眠的素衣。
这静默里,又沉淀着多少灼热的故事呢?于是,思绪便不由自主地,随着这纷扬的雪花,飘向历史的深处去了。雪,这冰冷的尤物,竟常常做了热血传奇最凛冽的背景。“雪拥蓝关马不前”,韩退之那一腔忠愤,满腹委屈,在蓝关的厚雪前,化作了英雄失路的苍凉。马儿踟蹰不前,是畏那自然的风雪,还是惧那人世的风霜?那雪,拥住的岂止是关隘,更是一颗被放逐的、滚烫的儒者之心。“卧冰求鲤”的王祥,将那赤裸的胸膛,贴在彻骨的寒冰之上,只为求得一尾鲜鱼,疗养继母的病体。那份孝心化成的热,是否能将身下的冰层,融开一个小小的、温暖的孔洞?这故事听来有些迂执了,可那冰天雪地里迸发出的人性至善的光辉,却比任何炭火都要灼亮。千古的憾事,也常常由雪来见证。屈子的《离骚》,香草美人,上天入地,忧愤何等的深广!然而那楚地的烟波与云梦大泽的水汽,孕育了他瑰丽的想象,却似乎未曾孕育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。我们翻遍那泣血的篇章,寻不见雪的踪影。这是否也是一种天意的缺憾?倘若有一场大雪,落在他行吟的江畔,落在他“冠切云之崔嵬”的高冠上,是否能稍稍冷却他心头的焦灼,或是将那浑浊的世道,映照得稍微清白一些?我们不得而知了。只知到了《诗经》里,那远戍的征人归来时,景况已是“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。去时杨柳依依,是青春,是希望;来时雨雪霏霏,是沧桑,是倦怠。那雪,便成了时间流逝最直观的注脚,成了家园记忆里最后一道苍茫的、混合着慰藉与伤感的布景。
这雪,于是便纷纷扬扬地,落满了整个中国的文学与历史,每一片都带着不同的体温与情感。易安居士的雪,是精巧而蕴藉的,“雪里已知春信至,寒梅点缀琼枝腻”。她能在彻骨的寒冷里,敏锐地捉住那“春信”的纤毫,那一点梅的红,便是她心头未灭的、对美好生活纤细而执拗的期盼,在茫茫白色中,绽出的一星倔强的火苗。东坡居士的雪,则豁达得多了。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”他遭遇的,或许是雨夹雪,或许是人生的风雪,但他竹杖芒鞋,一蓑烟雨(或是风雪),便将其视作自然的馈赠。那雪落竹叶的沙沙声,落在他宽大的蓑衣上,不是打击,反成了伴奏他吟啸的天然清音。这是何等的胸襟!能将一切困厄,都内化为生命风景的一部分。李太白笔下的雪,是夸张的,是盛唐气魄的溢出,“燕山雪花大如席,片片吹落轩辕台”。这哪里还是自然的雪,这分明是他胸中块垒,是他瑰丽想象的喷薄,是那个时代磅礴精神的外化。而杜工部的雪,则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,“夜来城外一尺雪,晓驾炭车辗冰辙”。那卖炭翁的辛酸,那官使的骄横,都被这一尺白雪,映照得格外分明。雪成了背景板,衬出人世的不平,冷冷的,带着讽刺的锋芒。到了曹雪芹那里,雪更是终结的象征,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,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那场覆盖了贾府、覆盖了大观园、也覆盖了整个旧梦的大雪,是悲剧的终点,是繁华的葬礼,也是一切归于空无的、最后的、也是最干净的句号。一场雪,便是一场缩微的人生;千古的雪,便是千古人生的总和,有的热烈,有的凄清,有的超然,有的沉重,最终,却都静静地落在这片土地上,叠成一层又一层文化的冻土。
这冻土,并非死寂。我们的文明,便是在这雪地里,深一脚、浅一脚,蹒跚而又无比坚定地走出来的。这行走,有时是诗意的。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,那是一种退守到极致的孤高与自持,在绝对的寂静与寒冷中,钓的或许已不是鱼,而是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那份禅意。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”,杜甫草堂的方寸窗口,竟能收纳千年的积雪与万里的行程,这是何等的时空胸怀!这雪,便成了连接刹那与永恒、咫尺与天涯的灵媒。这行走,更是历史的,充满了热血与烽烟。李愬雪夜入蔡州,一场出其不意的大雪,掩护了奇兵的脚步,成就了中唐一场堪入兵典的奇袭。那夜的雪,是智慧的同盟,是胜利的羽翼。而到了北宋的末年,雪却成了耻辱与苦难的见证。徽钦二帝,连带着他们的妃嫔臣僚,在冰天雪地里被押往北国,那一路的雪,该是浸透了皇室的血泪与一个王朝最后的体温吧?可讽刺的是,偏安一隅的南宋,在“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”的暖风熏醉里,临安的宫阙中,或许正欣赏着庭前的飞雪,将其当作助兴的雅玩。同是赵宋的雪,落在汴梁是铁蹄下的寒刃,落在临安却成了玉壶光转间的点缀。这其间历史的吊诡与民族的伤痛,又岂是一场雪能说得清?月色与雪色之间,确乎有一种绝色,那便是人间的血色与历史的成色混合成的、第三种不容逼视的、沉重的色彩。
这雪,一直下着,下到近古,下到现代。成吉思汗的铁骑,踏着漫天的风雪,将上帝之鞭挥向远方,那雪片沾满了刀弓,反射着冷冽的、扩张的野心。晚明的风雪,在张居正死后,似乎下得格外凄紧,送走了一位试图为帝国续命的能臣,也送走了一个王朝最后自救的气数。而在更北的苦寒之地,白山黑水间,那雪曾默默覆盖过抗争者的遗体,见证过一种不屈的、塞满了棉絮也塞满了信念的坚韧。最不能忘却的,是那支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队伍,在雪山草地间的跋涉。雪山的巍峨,草地的泥泞,都被他们用人类的意志,丈量成一条通向新生的道路。那雪,冷得刺骨,却也纯粹得彻底,仿佛要为他们涤尽一切旧世界的尘埃。而后,一个湖南口音的声音,在陕北的塬上朗吟:“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,欲与天公试比高。”这已不是对自然雪景的客观描摹,而是一个崭新时代主体精神的磅礴宣告。那雪,在他眼中,不再是阻隔,不再是感伤的对象,而是奔腾的、充满生命力的、可与宇宙比肩的壮美意象。这雪,便从古典的意境里,一跃而进入了现代史诗的宏阔篇章。及至殷秀梅那浑厚圆润的歌声响起,“我爱你,塞北的雪……”,那雪又被赋予了家园的、母亲的、滋养万物的柔情。一片雪,就这样从《诗经》的河畔,飘过唐诗宋词的檐角,落进革命的烽火与建设的歌声里,层层叠叠,堆叠成一部厚重无比的、白色的华夏文明史。
雪,终究又不独是中国的。它静静地落在地球的每一处角落,因着地域与人情的不同,幻化出万千种姿态与意义。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,或许终其一生,也无法想象这冰冷的、柔软的、从天而降的白色晶体为何物。他们的神话里,只有灼热的太阳、咸味的海风与丰饶的雨水。而在北极,在爱斯基摩人(我更愿称他们因纽特人)的生活里,雪是伙伴,是屏障,是材料,更是语言的精髓。据说他们的语言里,有一百多个词汇来描述不同状态、不同情境下的雪。那是一种生存智慧对自然最细腻的解读,每一种雪,都与他们的捕猎、出行、筑屋息息相关。这雪,便不是风景,而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了。
海明威凝望着乞力马扎罗山顶那永不消逝的雪,那雪成了他笔下主人公追求的精神高度,一种纯粹、不朽的象征,与山脚下热带草原的躁动与死亡,形成残酷而迷人的对照。西伯利亚的冻土里,厚重的冰雪将猛犸象巨大的身躯与时光一同封存,像一个关于远古的、白色的梦,不知何时才能甦醒。阿尔卑斯山巅的雪,在希腊神话的余晖里,似乎还闪烁着宙斯的雷霆威光,是神力永恒的、冰冷的冠冕。莫斯科城外的冰雪,则两次成为俄罗斯的“冬季将军”,冻僵了拿破仑与希特勒不可一世的雄兵,那雪,便成了保卫家园最沉默也最强大的战士。
雪也落在文学的世界里,带着不同的民族性格。屠格涅夫笔下的俄罗斯原野的雪,是细腻而广袤的,带着一种沉郁的抒情,覆盖着贵族庄园的没落与知识分子彷徨的足迹。踏着那厚厚的积雪,走向西伯利亚流放地的,是十二月党人与他们那些勇敢的妻子们,那雪地上深深的脚印,是通往苦难的,却也是通往理想与爱情的。勃朗特姐妹笔下,英格兰荒原上的风雪,则呼啸着如同鬼魅,能吞噬庄园,也能将人心里的疯狂与偏执催生到极致,《呼啸山庄》里那永不停歇的风雪,几乎就是人物内心风暴的外化。而保尔·柯察金在乌克兰冰天雪地里修筑铁路的场景,那雪与冰,则是锤炼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”最艰苦的熔炉,雪的冷,反衬出信仰的热。到了东方,川端康成眼中的雪国,是“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,便是雪国”那般孤寂与洁净,艺妓驹子映在雪景镜中的容颜,美得虚幻而哀伤,那是日本美学里独有的“物哀”与“幽玄”。最让人心碎的,是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,她在除夕夜的雪地里,划亮的每一根火柴,都映照出一个温暖的幻梦,那雪,是现实的残酷背景,而她微弱的火光与最终在雪中“微笑”的离去,却点亮了人类永恒的对温暖与光明的渴望。
我的思绪,便在这漫天飞舞的、跨越时空的雪花中,有些迷乱了。天山的雪莲,昆仑的玉峰,是边塞诗里永恒的、雄浑的意象;寒江独钓的孤舟,窗含西岭的千秋雪,是文人画里澹远的、精神的留白。哪里的雪,不曾默默注视过人类的悲欢、创造与毁灭呢?哪一片海洋的浩瀚,其源头不曾是高山之巅那一片圣洁的冰雪呢?雪花与浪花,一者静默地开在空中,一者喧哗地开在水面,开的都是这人间世,壮阔而又微末的风景。
但这风景的极致,或许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达到顶峰。地球最高处的雪,静静地覆在西藏的珠穆朗玛峰顶。那是众山的殿堂,是冰雪的王国,是离天最近的一片纯白。它不言不语,却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与雄心。那是一种终极的挑战,也是一种极致的宁静。大雪飘飘,自那巅峰落下,汇成涓滴,聚成溪流,终成江河,浩浩汤汤,东流入海。这雪的旅程,何其漫长,又何其壮丽!它从最冷的极致出发,去完成最动的奔流。
雪,便是这般矛盾而统一。它柔顺,可以任风摆布,塑造成任何形状;它又狂野,可以形成暴风雪,掩埋一切道路与踪迹。它覆盖,仿佛要将一切差异抹平;它又映照,能将最细微的凹凸显影。这多像我们的人生,多像我们民族走过的路。昨日之雪,是文明的肇始,是《诗经》里“雨雪霏霏”的古老歌谣,是诸子百家在雪夜围炉的深邃思辨,它奠定了我们精神的底色——那是一种在寒冷中寻求温暖、在静默中聆听大道、在纯净中映照本心的底色。今日之雪,是民族的复兴,是雪山草地淬炼过的信念在新时代的延展,是“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”那般主动把握命运的豪情,在现实大地上的生动实践。这雪,依旧在下,落在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上,落在飞驰的高铁车窗边,落在依旧在田间辛勤劳作的老农的蓑衣上,也落在实验室里凝视着窗外、思索着未来的科学家的眼镜片上。它连接着古老的静默与现代的喧腾,连接着历史的厚重与未来的轻盈。
窗外的雪,不知何时,已变得稀疏了。天色却并未开朗,依旧那样沉郁地灰着。地面上,已匀匀地铺了一层白毯,柔软地盖住了枯草的颓败,盖住了泥土的黝黑,将一切棱角与污秽,都暂时收纳进它宽和的怀抱里。世界显得安静了,也干净了。这洁白的礼服,是冬天送给大地最后的、也是最郑重的礼物。
我忽然想起那些写雪的句子来。它们像一片片不同的雪花,从不同的时空飘来,落在我的心上。“大雪纷纷扬扬落下,那一片雪花在空中舞动着各种姿势,或飞翔,或盘旋,或直直地快速坠落,铺落在地上。”这是动态的观察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这是惊喜的比喻。“雪让人的感觉只有一个字——冷。”这是最直白的身体感受。“我认出,那些雪地上凌乱闪烁的脚印,是诗;而被踩得黯淡板结的路,是散文。”这已是心灵的感悟了。还有那忧伤的句子,“在忧伤中,我们学会了坚强……当黑色的雪融化在天空里的时候,忧伤依然会给我带来幸福。”雪,竟也能是黑色的么?或许,那是指生命中那些沉重的、阴郁的时光,它们如雪一般覆盖一切,寒冷彻骨,但融化之后,或许也能滋养出新的生机。
雪花、浪花,究竟哪个更像人生?是浪花的热闹与易碎,还是雪花的静默与短暂?或许都是。浪花跃起那一刻,竭尽全力,绽放所有的洁白与力量,然后迅速回落,泯然于众。雪花悠悠飘落,看似从容,却也无从选择自己的归宿,或化于掌心,或归于尘土,或积成一片令世界改观的素净。它们都美好,都短暂,都身不由己,却又都在自己的轨道上,完成了属于自己的、独一无二的“落”或“跃”。
雪,快要停了。最后的几片,犹犹豫豫地,在空中打着旋儿,仿佛对这人间还有无限的留恋。我静静地看着。这今日的雪,究竟是谁的雪呢?是谢道韫的?是杜甫的?是教员的?是因纽特人的?是海明威的?还是那个在街头匆匆赶路、呵着白气的陌生人的?我想,它谁的都是,又谁的不是。它只是它自己,是水汽的凝华,是自然的馈赠,是时间飘落的鳞片。我们不过是偶然的看客,将自己各色的情感与记忆,投射到这一片纯白之上,便以为拥有了它,理解了它。
其实,我们何曾真正拥有过一片雪呢?就像我们何曾真正拥有过一滴水,一寸光阴。我们只是经过它们,被它们经过。在这经过与被经过之间,留下一点湿润的痕迹,或一点冰凉的记忆,如此而已。
然而,这也就够了。在这“今日”的雪将止未止的时刻,我能这样静静地看它,想它,让思绪随它飘荡千年,纵横万里,让心头被它拂过,留下一片清凉的安宁,这本身,不就是一场小小的、珍贵的相遇么?
明日,或许晴,或许阴,或许还有雪。但今日的这场雪,确乎是要尽了。它来得悄悄,去得也默默。大地穿上了它赠与的礼服,显得庄重而崭新。虽然我知道,这崭新是暂时的,风会来,日光会来,足迹会来,很快这洁白便会斑驳,便会消融,露出底下真实的、错综的、充满生命力的世界的本来面貌。
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?雪来过,静静地,覆盖过一切。这就很美了。
我推开窗,一股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,带着雪的、干干净净的味道。